


2018-05-09 09:1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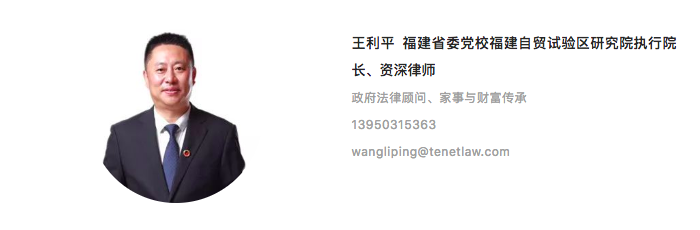
一、“公域”与“私域”
在英文中,president一词,既有校长之意,也有总统之意,足见校长如同总统,校长是知识王国的国王,总统是世俗世界的国王,均系有公众影响力之人,谓“公众人物”。社会大众关注“公众人物”的一言一行(甚至包括其私人生活),实属正常反应,因为,大众对“公众人物”是有期待的。他们把“公众人物”当做偶像来崇拜,不容许自己偶像有任何瑕疵。“公众人物”担负引领社会大众的重要使命,具有方向性作用,他们的一切都已属于“公域”,为了“公”,他们必须让渡了自己的“私域”。为此,大众不仅有“苛求”“公众人物”的权利,而且只有把他们置于阳光下,大众心理才踏实,才有安全感可言。
在古代,宫中有专门记录帝王言行的官员,所记录的言行汇编为《起居注》,主要包括:一是帝王的日常生活,每天吃什么,和哪个妃子共眠,去了什么地方,都清楚地记录在案;二是帝王处理朝政的情况,帝王每天看了多少奏折,做了哪些批示,工作多长时间,说了哪些话,也都一一记录。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尙矣。”从汉以后,几乎历代帝王都有起居注。今天,西方许多国家,担心掌权者公权私用,法律规定掌权者必须将隐私公开,掌权者不能以名誉受损为由,拒绝媒体监督。事实上,古代中国对帝王言行的记录,目的也在督促帝王勤政爱民,不滥用权力。
二、你不依我不饶——“苛求”权的依据何在?
依照通行标准,“公众人物”分为政治公众人物(官员)与社会公众人物(非官员)。前者主要指政府官员;后者主要指教科文卫界、娱乐界、体育界以及公益组织等社会名流。前者更多地涉及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舆论监督问题,后者则是因为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而在社会生活中引人注目,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在现行体制下,大学校长享受一定的行政级别,亦官亦学。
众所周知,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特别是监督批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自由,是民主国家的“生命线”。言论自由是指公民享有的受法律规定、认可和保障的,使用各种媒介传播发表意见、主张、观点、情感而不受任何个人或组织的干涉、限制或侵犯的权利。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言论自由的根本应是议政的自由。政治言论是否自由,才是一个社会有无言论自由的真正标准。而政治言论是否自由又以公民是否具有监督批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自由为判定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公民只有享有监督批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自由,才敢于和善于成为孜孜不倦的揭露者和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唯有如此,人民民主才不会徒具形式,人民当家作主才名符其实。
早在 1923年的美国的一个判决书就指出:“宁可让一个人或者报纸在报道偶尔失实时不受惩罚,也不能使全体公民因担心受惩罚而不敢批评一个无能而腐败的政府”。在1964年 L. B. 沙利文(L.B.Sullivan)诉金博士等4名牧师和《纽约时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对官员和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作特殊处理,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予以优先保护,其理由有二:一是这关系到对公众人物的舆论监督,《纽约时报》如果没有打赢这一官司,“那么以后类似的因报道有误而产生的官司还会接踵而来”,对公众人物实际上就会无法监督,因为一有事实的出入,就会认为是诽谤,议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就会受到伤害,因为“让新闻媒体保证每一条新闻报道都真实无错,那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有“个别细节失实,有损当事官员名誉 ”也不予制裁,“言论自由才有存在所需的呼吸的空间”;二是公众人物本人可以接触媒体,反驳所谓的“诽谤”。而“民众无权无势,在揭发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时怎么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呢?”。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陈志武,通过查阅美国过去100多年的案例库发现,在类似的涉及媒体名誉侵权的案件中,美国媒体败诉的可能性只有8%。自1987年以来国内发生的121个涉及各类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台等)的名誉侵权案中,中国媒体的败诉率竟然高达70%。
2002年12月,在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纠纷案中,上海静安区法院的判决书指出:“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这是我国司法涉及“公众人物”名誉侵权一起典型判例,“公众人物”必要的容忍和理解,是公民舆论监督权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
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快乐,大人物有大人物的烦恼,公众人物影响了大众,也要接受大众的“苛求”,大众怕被公众人物“带坏”,更害怕公众人物借自己的影响力“侵蚀”了公民的权利,法治国家应有对“公众人物”予以限制的制度安排。
有裂缝的地方有风,有雨,也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