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17 10:4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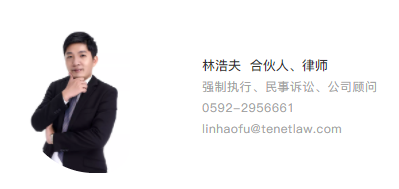
申请人大成产业气体株式会社、大成(广州)气体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就其在协议中所约定的仲裁条款的效力产生争议,并于2020年1月20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申请。双方在协议中约定,“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对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当事人应首先尝试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同意将该等争议最终交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其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并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就此条款而言,属于约定“外国仲裁机构在国内仲裁”的条款,一直以来就存在较大争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受理这一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后,经审理裁定“争议最终交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其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的仲裁协议有效,并且对于我国仲裁法并未允许外国仲裁机构在国内仲裁的观点进行了全面而有力的回应,法院认为:(1)仲裁是当事人自愿解决争议的方法之一,就当事人自愿解决争议的实质而言,它不涉及我国仲裁市场是否开放的问题。(2)最高人民法院的[2013]民四他字第13号复函已经确认了此类仲裁协议的效力,而复函作为司法解释的形式之一,具有法律效力。(3)中国对境外仲裁机构在国内仲裁并无明令无禁止性规定。(4)对于具体案件,司法不能以立法不明为由拒绝裁判。
此“大成”一案,可以说与“龙利得案”一脉相承,并有力巩固了当年的司法实践成果,更是为将上海打造成亚太仲裁中心的战略目标打响了极为响亮的一枪。
回顾历史,外国仲裁机构在国内的仲裁可谓历经坎坷。
一、何为“非内国裁决”——回顾“旭普林案”和“德高案”
在“旭普林案”和“德高案”中,将外国仲裁机构在国内的仲裁视为“非内国裁决”,进而引发了对于裁决籍属标准的争论。对于国际商事仲裁而言,裁决是否应具有一国的国籍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商事仲裁应最大限度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仲裁裁决不应具有一国国籍;持肯定观点的另一方则强调,讨论仲裁裁决的国籍问题十分重要且必要,属于关乎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事项的“先决问题”。
根据我国加入《纽约公约》时所作的互惠保留声明,中国只在互惠的基础上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公约,这意味着,我国实际上排除了对“非内国裁决”的执行。
重温“旭普林案”,申请人德国旭普林国际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无锡沃可通用工程橡胶有限公司因申请承认和执行国外仲裁裁决一案在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于2006年7月19日审结。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4)锡民三仲字第1号裁定书中认为,“本案系承认和执行国外仲裁裁决案。中国系《1958年纽约公约》的缔约国,且根据《1958年纽约公约》第一条规定,本公约对于仲裁裁决经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认为非内国裁决者,亦适用之。本案被申请承认和执行的仲裁裁决系国际商会仲裁院作出,通过其总部秘书处盖章确认,应被视为非内国裁决。且双方当事人对适用《1958年纽约公约》均无异议,因此本案应当适用《1958年纽约公约》。”虽然本案裁决地为上海,但由于当时对于裁决籍属判断并不以仲裁地为标准,而是以仲裁机构所在地作为判断仲裁裁决的籍属标准,因此作为“非内国裁决”,违背了我国的互惠保留声明,是无法被承认与执行的。另外,本案仲裁裁决所依据的仲裁条款因先前已被我国法院认定为无效,故本案仲裁裁决最终被认定为具有《1958年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项所列(甲)情形,裁定不应得到承认和执行。
在“德高案”中,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甬仲监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再次确认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内地(仲裁地:北京)作出的仲裁裁决是“非内国裁决”。与“旭普林案”相同的是,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采取了“仲裁机构所在地”作为仲裁裁决的籍属标准。与“旭普林案”不同的是,其认为该案不存在拒绝承认与执行所涉仲裁裁决的理由,裁定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但显然,根据我国加入《纽约公约》时的互惠保留声明,我国法院是不得依据《纽约公约》来承认和执行“非内国裁决”的,“德高案”的裁定违反了我国的互惠保留声明。
二、“仲裁地”还是“机构所在地”——仲裁裁决籍属标准的转变
对于仲裁裁决籍属,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不予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10334/AMW/BWD/TE最终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04]民四他字第6号)中也是以仲裁机构所在地作为判断标准,复函指出:本案所涉裁决是国际商会仲裁院根据当事人之间达成的仲裁协议及申请作出的一份机构仲裁裁决,由于国际商会仲裁院系在法国设立的仲裁机构,而我国和法国均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成员国,因此审查本案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应适用该公约的规定,而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的规定。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仲裁裁决籍属标准的适用发生了转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执行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09]415号)指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做出的临时仲裁裁决、国际商会仲裁院等国外仲裁机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安排》的规定进行审查。不存在《安排》第七条规定的情形的,该仲裁裁决可以在内地得到执行。在这一通知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外国仲裁机构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认定为香港裁决,适用了仲裁地标准,从此逐渐改变了以“仲裁机构所在地”为仲裁裁决籍属标准的司法倾向。
紧接着,在2010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关于申请人 DMT 有限公司(法国) 与被申请人潮州市华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被申请人潮安县华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2010]民四他字第51号)中指出“本案系申请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新加坡)国际仲裁院做出的第13450/EC号仲裁裁决案。中国和新加坡均是《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因此,涉案仲裁裁决是否可以得到承认和执行,应当按照《纽约公约》的规定进行审查。”意即将国际商会仲裁院在新加坡作出的仲裁裁决视为新加坡仲裁,而不再视为法国仲裁,这又是适用仲裁地标准认定仲裁裁决籍属的又一实践。
三、“仲裁委员会”定义之惑——“神华煤炭案”与“龙利得案”
除了仲裁裁决籍属问题,外国仲裁机构能否在我国开展业务,关系到约定“外国仲裁机构在国内仲裁”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对于《仲裁法》第二十条“仲裁委员会”是否包括外国仲裁机构,在司法实践中也历经了180°的态度转变。
在神华煤炭运销公司与马瑞尼克船务公司确认仲裁协议之诉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4日作出了[2013]民四他字第4号《复函》,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系针对仲裁法第二十条作出的司法解释。仲裁法第二十条所指的仲裁委员会系依据仲裁法第十条和第六十六条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并不包括外国仲裁机构。故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并不适用于外国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效力作出认定的情形。”该复函对《仲裁法》第二十条的“仲裁委员会”作了严格的解释,将外国仲裁机构排除在外,而这使得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进行仲裁的合法化遥遥无期。
令人惊讶的是,在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最高人民法院竟然转变了观点。2013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3]民四他字第13号《复函》,就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安徽省龙利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BP Agnati S.R.L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作出回复,“本案为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案件。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因合同而发生的纠纷由国际商会仲裁院进行仲裁,同时还约定‘管辖地应为中国上海’(PLACE OF JURISDICTION SHALL BE SHANGHAI,CHINA)。从仲裁协议的上下文看,对其中‘管辖地应为中国上海’的表述应当理解为仲裁地在上海。本案中,当事人没有约定确认仲裁协议效力适用的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应适用仲裁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来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涉案仲裁协议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约定了仲裁事项,并选定了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应认定有效。同意你院关于仲裁协议有效的多数意见。”与“神华煤炭案”不同,在此《复函》中,最高人民法院对“仲裁委员会”作了宽松的解释,认定“仲裁委员会”可以包括国际商会仲裁院等外国仲裁机构。
相较而言,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内部的少数意见认为,设立仲裁委员会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行政部门登记,仲裁在我国是需要经过行政机关特许才能提供的专业服务,我国政府并未向国外开放我国的仲裁市场,故外国仲裁机构依法不能在我国境内进行仲裁。笔者认为,该少数意见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提供仲裁服务是否需要经过行政审批在当时确实是个值得商酌和探讨的问题。但是从最高人民法院态度来看,逐步放开我国的仲裁市场正是未来的趋势,否则最高人民法院不会改变以往不认可约定“外国仲裁机构在国内仲裁”的仲裁协议效力的立场,开始承认此类条款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四、国家政策与司法文件的引导
自“龙利得案”后,我国仲裁市场的开放态势在国家政策和司法文件的引导下积极推进、不断发展,外国仲裁机构在国内的仲裁可以说是已经迎来曙光和机遇。
2015年4月8日,国务院批准《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国发[2015]21号)第11条明确要“支持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入驻”,并欲将上海打造成“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而此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国际商会仲裁院、韩国商事仲裁院等全球知名的国际仲裁机构纷纷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代表处。
就在去年7月27日,国务院又发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明确“允许境外知名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登记并报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在新片区内设立业务机构”,除此之外,亦明确可以“就国际商事、海事、投资等领域发生的民商事争议开展仲裁业务”。
同年11月8日,在上海国际仲裁高峰论坛上,上海市司法局正式发布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设立业务机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2020年1月1日起,符合规定条件的在外国和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合法成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仲裁机构以及我国加入的国际组织设立的开展仲裁业务的机构,可向上海市司法局提出申请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登记设立业务机构,开展相关涉外仲裁业务。在《管理办法》第14条,详细列举了业务机构可以开展的涉外仲裁业务范围,包括在(1)案件受理、庭审、听证、裁决;(2)案件管理和服务;(3)业务咨询、指引、培训、研讨。
紧接着,在2019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法发[2019]31号),其中第6条,连用七个“支持”,表达了将对外国仲裁机构在国内的仲裁提供丰富的司法保障。其中,“依法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一句最令人关注。此前,对于仲裁裁决的籍属判断标准已由“仲裁机构所在地”逐步向以“仲裁地”发展,本次“依法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提法,意味着若外国仲裁机构在国内仲裁,将被视为“我国的涉外仲裁裁决”,而不再是“外国仲裁裁决”或“非内国裁决”,再次肯定了以仲裁地为标准识别仲裁裁决籍属的做法。
五、结语
外国仲裁机构在国内仲裁的发展,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在不断的自我肯定与否定的螺旋式前进道路上逐步放开和发展起来的。伴随着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司法实践的全方位引导,上海,未来亚太仲裁中心的定位,必将吸引更多国际仲裁机构前来开展仲裁业务。不光是上海,应该说在未来,对外国仲裁机构在国内的仲裁裁决,采用更加开放的态度进行接纳、引导和管理才是我国对外加强经济交往、通过社会主义法治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必然趋势,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