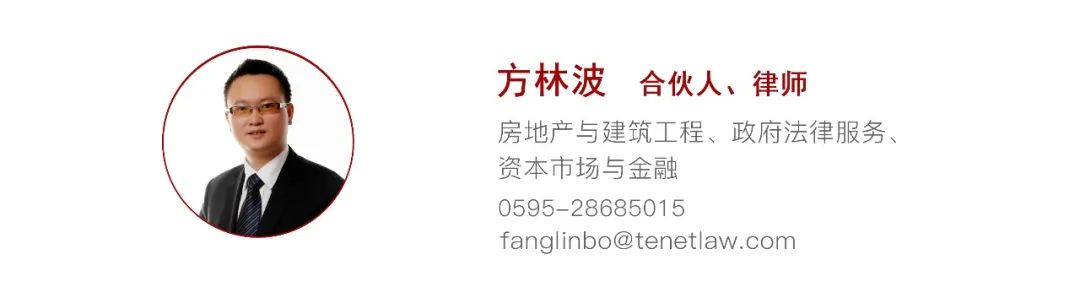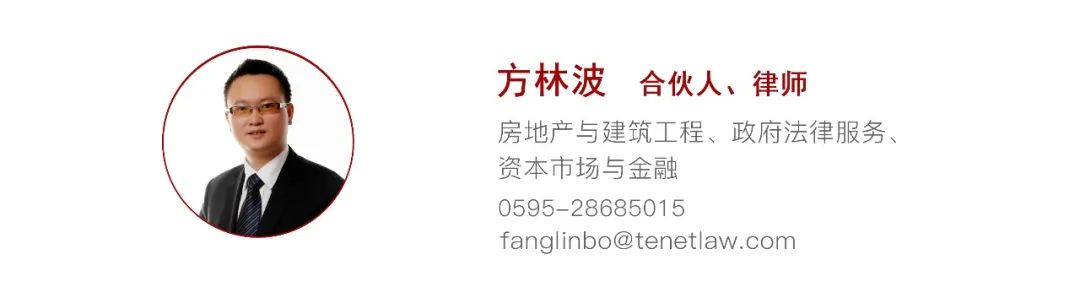

一、时代背景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背景
近年来,互联网的兴起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发展轨迹、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关键要素,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不正当竞争行为和互联网不可避免地产生交汇,竞争的方式不断创新,竞争的因素不断增多,竞争的范围不断拓展。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被互联网的浪潮裹挟前行,原本的法律规定已难以解决如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变化,因而2017年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正是面对互联网给竞争行为带来的深刻变化而作出的必然选择,也是对时代发展的回应。基于此,《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工作应运而生,并于2017年11月4日通过了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二)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亮点
新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有两个亮点:第一是明确了第二条具有一般条款的性质,有利于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应对层出不穷的不正当竞争方式时,能够作出更加及时恰当的判断;第二是增设了互联网条款,不仅适应了互联网治理的时代要求,而且,立法机构在这过程中也汲取了司法审判机关与行业治理的有益经验。然而,对原本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修订并无法一劳永逸,在司法实践中,仍然需要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般条款与“互联网条款”的适用问题进一步进行磨合和调整。
二、一般条款与“互联网条款”的
司法适用困境
有关互联网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传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互联网领域的延续,例如利用虚假宣传,商业诋毁等方式进行市场交易行为的这类案件,但其法律定性相对稳定,互联网这一因素的介入并未影响其法律定性,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从容应对。另一种类型是互联网新型案例,这种类型的案例不能被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传统类型覆盖,只能把这类案件的规制寄托于2017年新修订的第12条互联网专条,但是第12条明显力不从心。更多涉及互联网的反不正当竞争案件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2条一般条款,并非适用第12条来解决。
据学者统计,截至2018年底,在互联网相关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法》被引证判决的案例中,大约有超过60%的案件将一般条款作为裁判依据。为了证实这一统计,笔者近期利用软件进行案例检索,发现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以后的近三年来,援引第2条进行裁判依据的案例达四千多起,而适用第12条进行裁判的案例还不足两百起。在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的这几年,互联网条款被引用的频率并不高,在适用过程中面临着重重障碍。
三、司法适用困境的原因
(一)典型案例
以下对互联网典型案例——“爱奇艺诉搜狗案”的案情及判决依据予以分析,以期能发现、整理出“互联网条款”在司法实践运用中的主要问题以及造成司法适用困境的原因。
爱奇艺公司是爱奇艺网站的运营商,搜狗公司是搜狗输入法软件的提供者。搜狗公司被指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行为方式是:当手机用户在浏览器中进入爱奇艺网站,使用搜狗输入法输入要搜索的视频时,搜狗输入法会自动启动“搜索候选”功能。点击后,用户会被定向到“搜狗搜索”页面,会出现搜狗公司关联公司的同一剧集的播放链接。爱奇艺认为搜狗公司误导用户将“搜索候选”功能认为是“输入候选”,极易使用户产生误会,引诱用户进行点击,从而使网页跳转至搜狗公司的搜狗搜索,并呈现其关联公司搜狐视频,损害了爱奇艺网站的利益,该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一审判决书中,原告爱奇艺公司认为被告违反了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一般条款”和第 12 条“互联网条款”的规定,但法院最终仅以“一般条款”为依据进行论述,没有分析原告提出的“互联网条款”。一审法院认为,搜狗公司在搜狗输入法中设置“搜索候选”功能没有不当之处,对爱奇艺公司和消费者没有不利影响。同时,由于很难要求平台运营商审查该软件下的“搜索候选”功能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因此判决驳回了爱奇艺公司的诉讼请求。
在二审中,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为,被告行为的干预可能导致部分交易机会和搜索流量从爱奇艺转移到搜狗及其关联公司,爱奇艺遭受的损失是客观的。然而,市场竞争的主要表现是对交易机会的竞争。只有当被指控的行为违反商业道德时,该行为才会被追究责任。要全面调查涉诉行为对爱奇艺公司运营、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市场竞争秩序的影响。
首先,爱奇艺的正常运营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阻碍和干扰。第二,被诉的行为并没有完全避免用户产生混淆,但市场选择功能并没有真正被打破。最后,搜狗输入法同时具有“搜索候选”和“输入候选”两个功能,这是一项技术创新。创新往往来自于运营商的技术或商业模式之间的激烈碰撞。
该行为并未过度阻碍爱奇艺网站的正常运营,未达到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程度。综上所述,搜狗公司的行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从案例中总结司法适用困境的原因
从以上案件判决中不难看出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一般条款与“互联网条款”司法适用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互联网条款”被援引的频率并不高,造成这种司法困境背后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立法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新法第12条是对先前典型案例进行类型化区分并高度概括的产物,无法与网络的迅速发展的步伐相一致,“互联网条款”的规定也无法涵盖所有的新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二,就大多数诉讼案件而言,为了增加胜诉的筹码,原告即使能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互联网专条胜诉,也更愿意加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进行双重保障;
第三,研读“互联网条款”的兜底条款,会发现其适用的前提是,对于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进行了妨碍或者破坏,而在互联网领域竞争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竞争者经常进行的是有限的干扰行为,很少能达到妨碍或者破坏正常运行的程度,这也许是“互联网条款”适用困难的症结所在;
最后,就是形成了一般条款的适用路径依赖,这也是一般条款与“互联网条款”的最大的司法困境。在互联网条款增设以前,面对千变万化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司法机关习惯于运用一般条款进行分析说理,并依据一般条款来判决,因此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以至于在网络条款增设以后,这一路径依赖是否能打破、要如何来打破变成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因此,除了需要对“互联网条款”进行细化和不断完善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明确和优化一般条款与“互联网条款”的适用和联系。
四、对一般条款与“互联网条款”的
司法适用意见
(一)对一般条款的适用应保持谦抑态度
由于市场竞争的千变万化,法院援引一般条款来维持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无可厚非,但是一般条款是一种原则性规定,其具体适用缺乏明确的、可预见的标准,因此,滥用一般条款不利于维护司法公信力。
在一般条款限制性适用的理念之下,对该条的司法适用应始终保持谦抑的态度。凡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已有特别条款作出规定的行为方式,则不应适用一般条款。司法机关应充分理解一般条款原则性规定的性质,不能把一般条款视作不正当行为的具体裁判标准。
如前文所述,新法未修订前,在处理新型网络竞争行为时,法院往往因为无法引用具体条款而直接引用一般条款。为改变这种情况,在2017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立法部门以案例类型化的方式引入了“互联网条款”。由此可见,“互联网条款”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制互联网竞争行为的特别规范。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凡是属于“互联网条款”已明文禁止的网络竞争行为,均应适用特别规范,而不再援引一般条款。
(二)关于“互联网条款”中兜底条款的适用
“互联网条款”第2款前3项列举了三种具体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但这只是有限的类型化,难以适应现实的不断变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增设兜底条款无疑会使得立法体系更加完善,更能适应新时代的变化。
从具体表述来看,兜底条款所规制的是“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其他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除了将规范的行为限制在互联网范围内,该兜底条款的适用与一般条款非常难以区分,容易导致二者的适用产生紊乱。兜底条款难以适用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含义宽泛、没有明确适用规则。如何判断“妨碍”“破坏”和“正常运行”在司法实践上也是一个难题。
对此,通过法律修订的途径对兜底条款的表述加以完善的确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但法律修订程序繁琐、耗时较久,难以解决现今的问题。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为兜底条款的适用提供引导才是当下应当关注的重点。应严格限制第十二条“兜底性条款”的适用,司法适用在对“其他妨碍、破坏”和“正常运行”进行分析时,可以利用体系解释的方式加以限定,防止产生不合理的扩张解释。“其他妨碍、破坏”行为的表述意味着互联网专条的兜底条款规制的行为类型应与前三项列举的行为具有极高的相似性,不能覆盖所有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一般条款的适用
并非所有在互联网领域的竞争行为都应适用“互联网条款”。虽然一些例如诋毁商誉、虚假广告等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竞争行为既可以发生在传统商业领域,也可以发生在互联网领域,但互联网条款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限制,只有符合“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条件才可以适用互联网条款。而与上述特征不符的行为,即便与互联网相关,也无须适用互联网条款予以规制。因此,当某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既不属于互联网条款禁止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也不属于第二章规定的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又不正当地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时,可以考虑适用一般条款。
(四)一般条款和网络条款的具体适用路径选择
厘清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在面对具体案件时的司法适用问题就可以有所遵循。当某一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既可以适用一般条款,也可以适用互联网条款时,应当首先向互联网条款寻求依据,而不能率先依照一般条款,这是由一般条款和网络条款的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所决定的。而在互联网条款中,在满足“列举性条款”的规定情况时应先适用“列举性条款”,当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无法被“列举性条款”所涵盖时,应适用互联网条款的“兜底性条款”加以规制,但在适用“兜底性条款”时必须严格限制适用条件。只有当互联网条款的“兜底性条款”也难以涵盖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此时可以尝试适用一般条款加以规制。在选择适用一般条款之时,同样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严格限定一般条款的适用条件,即互联网条款的“列举性条款”和“兜底性条款”均无法评价该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穷尽其他条款时寻找不到法条依据时再适用一般条款;二是在适用一般条款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一般条款的适用要件,避免一般条款的滥用。
由此,当一般条款和网络条款的在适用中发生冲突或竞合时,其适用路径为:第一,尽量套用互联网条款中已经涵盖的类型;第二,经过充分说理论证后若发现该竞争行为不能为互联网条款的三种类型所涵盖,可以尝试运用兜底性条款,但是应注意产生不合理的扩张解释;最后,对于应用“互联网条款”确实无法进行说明的情形,可以尝试使用一般条款进行评价,但仍需遵循严格的论证过程,且做到贴合立法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