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5-06 11:0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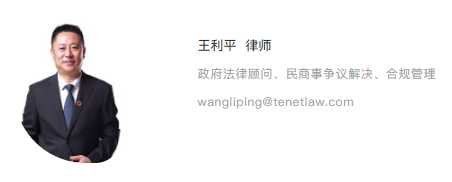
1215年,南宋迁都临安77年 ,一直处在金人南侵的困扰中。
1215年,忽必烈出生,蒙古人攻占燕京,金人已岌岌可危。
后,宋联蒙灭金。
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蒙古铁骑一路南下,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建立元朝,迁都燕京,称大都。
1278年,文天祥被元军抓捕,狱中作《正气歌》,从容殉国,流传千古。
南宋余部亡命天涯,1279年3月19日,崖山海战,走投无路,老臣陆秀夫背负儿皇帝跳海身亡,宋灭。
第2则
1215年,英国处在历史上最糟糕的国王约翰统治时期。
因,约翰王心中没神,无视贵族,任性。
果,约翰王好斗好战,横征暴敛,无知无畏,不讲信用。
遂,封城建邦的贵族们开始造反,兵临城下。
然,贵族们没有砍下约翰王的头,取而代之。
而,在坎特伯雷大主教斯提芬的见证下,1215年6月15日,于伦敦温莎城堡附近,泰晤士河畔,兰尼米德草场上,贵族们让约翰王在后人称为《大宪章》的文件上签上名字,此刻,不管约翰王内心有多么不愿意,他除了签名,已别无选择,这是他与贵族们妥协后的最佳选择。
《大宪章》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契约,贵族们赢得了权利,约翰王保住了王位。
约翰王在万人之上,在神和《大宪章》之下, “王在法下”成为执政底线,不容逾越,更不容践踏。
《大宪章》第61条明确了约翰王违约之法律后果:
余等之所以作前述诸让步,在欲归荣于上帝致国家于富强,但尤在泯除余等与诸男爵间之意见,使彼等永享太平之福,因此,余等愿再以下列保证赐予之诸男爵得任意从国中推选男爵二十五人,此二十五人应尽力遵守,维护,同时亦使其余人等共同遵守余等所颁赐彼等,并以本宪章所赐予之和平与特权。其方法如下:如余等或余等之法官,管家吏或任何其他臣仆,在任何方面干犯任何人之权利,或破坏任何和平条款而为上述二十五男爵中之四人发觉时,此四人可即至余等之前——如余等不在国内时,则至余等之法官前,一一指出余等之错误,要求余等立即设法改正。自错误指出之四十日内,如余等,或余等不在国内时,余等之法官不愿改正此项错误,则该四人应将此事取决于其余男爵,则此二十五男爵即可联合全国人民,共同使用其权力,以一切方法向余等施以抑制与压力,诸如夺取余等之城堡、土地与财产等等,务使此项错误终能依照彼等之意见改正而后已。但对余等及余等之王后与子女之人身不得加以侵犯,错误一经改正,彼等即应与余等复为群臣如初。国内任何人如欲按上述方法实行,应宣誓服从前述男爵二十五人之命令,并尽其全力与彼等共同向余等施以压力。余等兹特公开允许任何人皆可作上述宣誓,并允许永不阻止任何人宣誓。国内所有人民,纵其依自己之意志,不愿对该二十五男爵宣誓以共同向余等施用压力者,余等亦应以命令令之宣誓。如上述二十五男爵中有任何人死亡,离国或因故不能执行上述职务时,其余男爵应依己意自其他男爵中推选另外之人代之,其宣誓方法与上述诸人同。此外,上述二十五男爵于受托执行任务时,倘在出席讨论中关于某些事件发生争端,或有某些男爵被召请后,不愿或不能出席时,则出席男爵过半数之决定,或宣布之方案,应被视为合法且具有约束力,一如二十五人全体出席所议决者同。上述二十五男爵应宣誓对前列各项竭诚遵守,并尽力使其余之人遵守之,而余等亦不得由自己或通过他人自任何人取得任何物品致使上列诸权利与自由废止或削减。如有此项取得之物,应视同无效与非法,余等自己不得加以利用,亦不得通过任何别人加以利用。
依据上述第61条,在约翰王违反《大宪章》时,贵族拥有“造反”的权利。
第3则
1215年,南宋朝政一片昏庸,社会却一派繁华,市井文化崛起,江湖戏子演出时敢影射庙堂。
1215年,中国 “四大发明”均已问世运用。
1215年,造纸术尚未越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英格兰半岛,《大宪章》被贵族们用又尖又硬的鹅翎笔写在羊皮上 。
可是,“文明”的南宋并未有孕育出起而“造反”贵族集团,只是在忠臣与奸臣的道德标签里翻转。而且,南宋的“文明”也挡不住蒙古“野蛮”入侵,只留下文天祥《正气歌》作为最后的凭吊。
其实,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造反者,他还是摆脱不了黄袍加身的宿命,虽然,他是一个温柔的专权者。
甚至,宋朝出现过一群造反者,汇聚为一百零八条好汉,占据水泊梁山为王,一心等着招安,最后七零八落,死的死,残的残,整一个山寨水平。曾经豪气冲天的武松,终老归隐西子湖畔。
南宋最后在道德的阴沟里翻了船,连同“敌我”和“主奴”这两具僵尸,阴沟里冲天的臭气一直熏到现在。妥协被视为没有气节,造反被视为大逆不道。
美国《独立宣言》中写道: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
1215年英国贵族“造反”的权利,变为文明种子,乘坐“五月花”号船只,穿越大西洋,落户美洲大陆,鲜花盛开,硕果累累。
笔者说
如今,英国《大宪章》作为人类法治的开端,无可非议,因此,也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800年过去了,其间所包含的道理还在,从未过时,而且愈发显示其改变现实的力量。
法治首先体现为用法律约束最高统治者,正如《大宪章》约束约翰王。因此,法治不是掌权者依法治民,而是为掌权者设计制度笼子。
法治是力量妥协的产物,没有贵族的“造反”,就没有约翰王的退让。因此,法治需要足够制衡掌权者的力量,否则,就是墙上的饼。
法治不是圣人自觉的结果,更可能是恶人相互制衡的过程,最糟糕的约翰王诞生了最经典的《大宪章》。因此,法治非圣人之治,别期望圣人栽出法治之果,播下龙种,收获往往是跳蚤,圣人也成了历史长河里的跳梁小丑。
西谚云:“三个强盗出法治。”法治文明产生于野蛮与野蛮较量中,谁也消灭不了谁,结果,各方只好坐下来谈判,共同遵循彼此达成的协议,并有一个强有力的机制保障协议履行,以及对违约方的惩戒。可以说,法治往往是谈出来的,专制往往是打出来的。这个世界不怕有强盗,也避免不了强盗,小则盗钩,大则盗国。如果都是圣人,也就不需要法治了。渴望圣人的道德治国,时常误国,甚至亡国。
1215年,蒙古人正异军崛起 ,其后,横扫欧亚大陆,直抵法国多瑙河,如今,已烟消云散,仅剩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追忆,还得借助于金庸的武侠小说。1215年英国《大宪章》播下的法治种子,如今已遍布世界,成为共识,汇聚成浩浩荡荡的大潮,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这就是法治文明的力量,我们期待已久 。